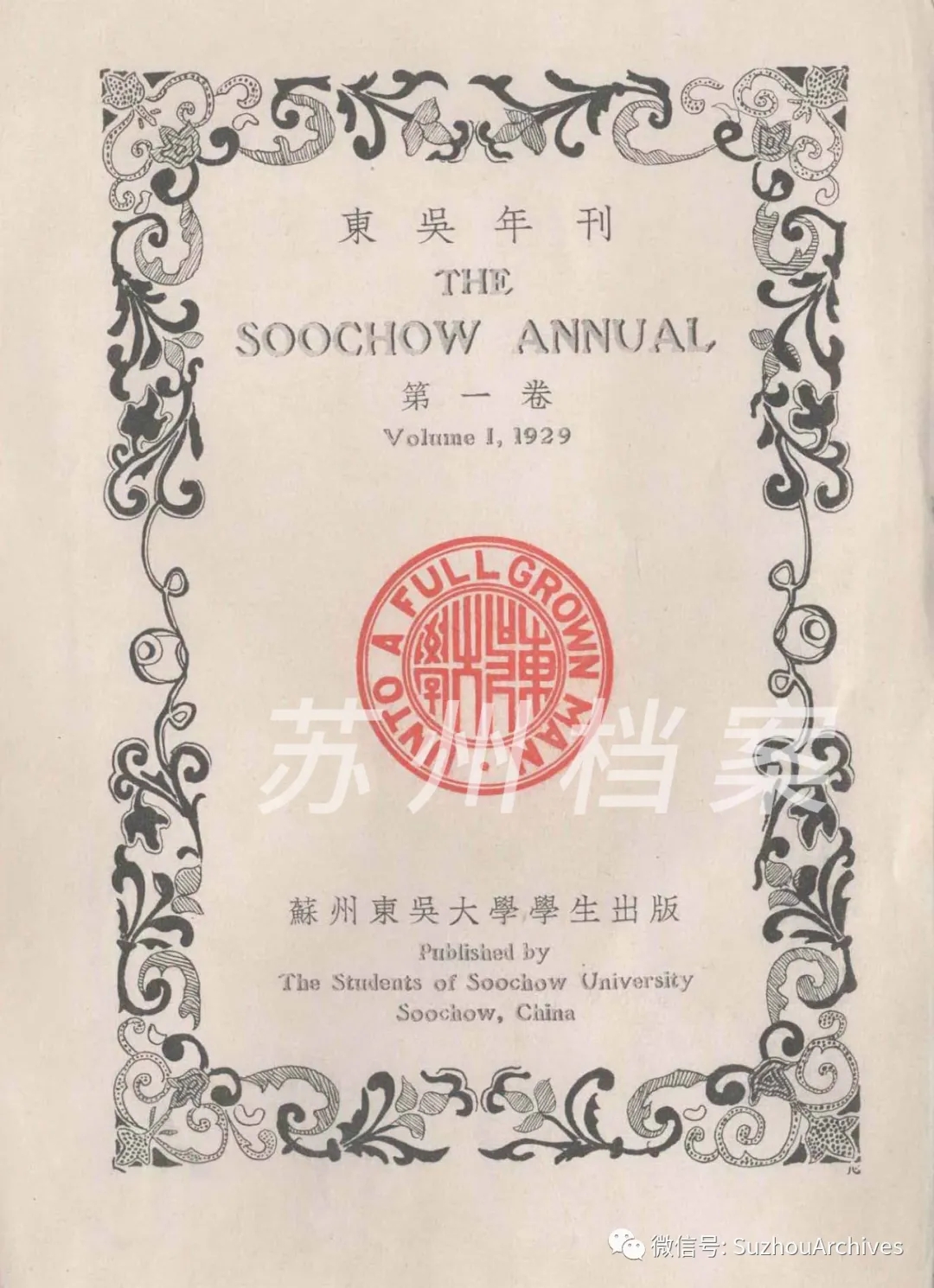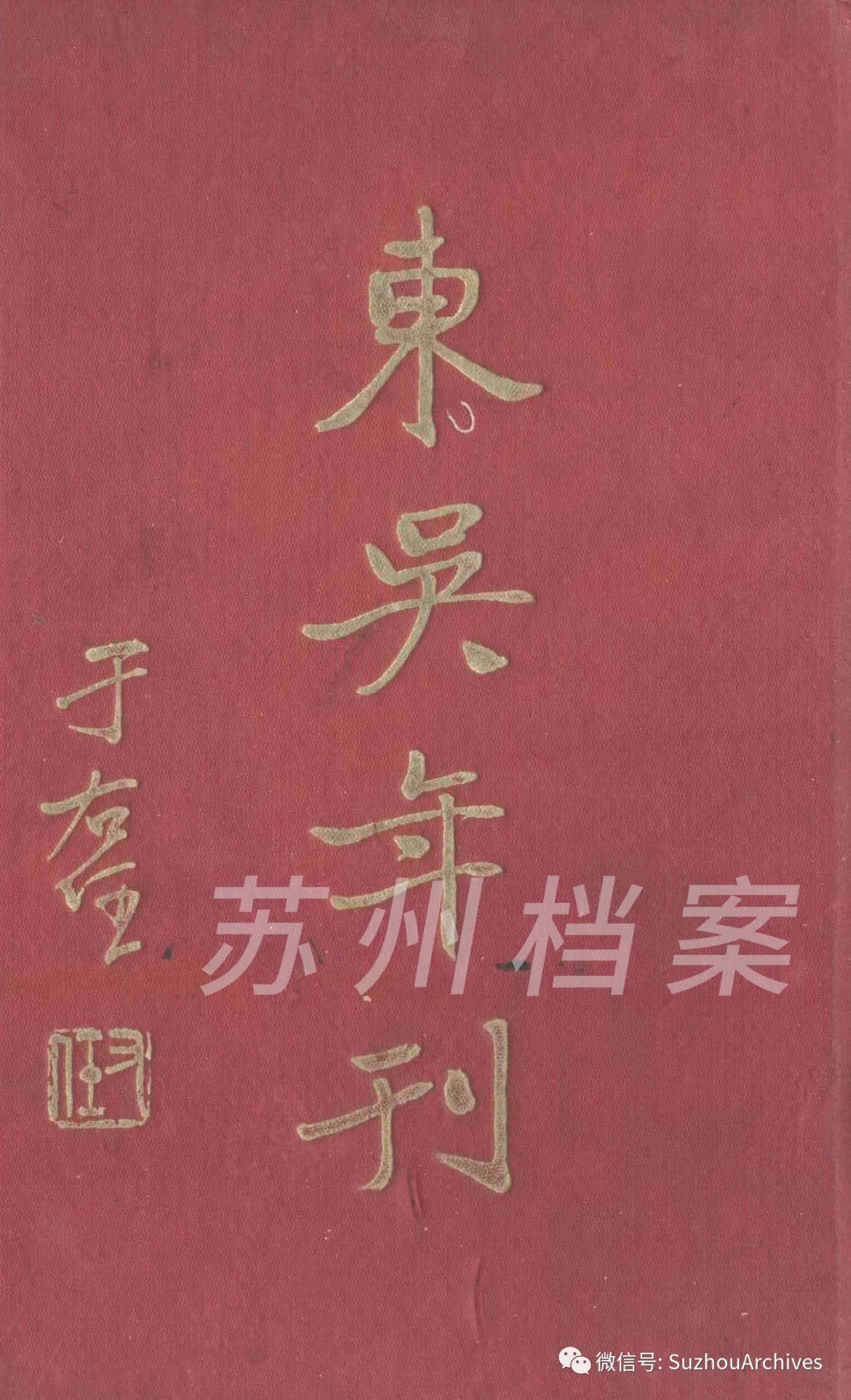| 中国第一部大学校史:《东吴六志》 | |||||
|
|||||
作者:杨旭辉 苏州大学档案馆珍藏着徐允修所撰的《东吴六志》,书中记载了早期东吴大学在教学、研究诸多方面取得的成绩。1926年甫问世,东吴大学国文教授薛灌英在序言中就说,从晚清开始,许多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“国中学校如林矣”,但始终以没有一部“胪陈始末之载记”的“学校过去史”为憾。薛氏所谓“学校过去史”,采用“以事别者”,详载学校“自始创而赓续相延之历史”,即是今日通行的校史。《东吴六志》弥补了这一缺憾,在当时就被视为前无古人的工作,就笔者不完全调查,《东吴六志》是目前所知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学校史。 徐允修,江苏吴县人,晚清贡生,东吴大学早期年资最深的教职员,“凡历博习、中西、东吴三易名以迄于今”。早在1897年,徐允修应东吴大学的前身博习书院之聘,任国文课教师。东吴大学创立后,他担任学校的中文秘书,从此三十年一直在校工作。徐允修对东吴大学校前世今生“知之綦详且确”,故而他“回想前尘”,将“记忆所及,与较有兴味者录存”,写成《东吴六志》。全书分六章,分别记载了学校的起源、设备、成绩、师资、生徒、琐言(按:指杂记)。因而,《东吴六志》对于考镜东吴大学最初的发展历程,理解创校之初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建设,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,也是第一手的原始文献。从中可以了解东吴大学的许多教育理念至今仍属先进,笔者将其中所述内容归纳为“放眼世界,顺应潮流,中西融合,融会贯通,博雅淹通,务实创新”数语,或径可称之为“东吴经验”。具体说来,有以下四点认识,实可为今人借鉴: “相互考证,免除隔膜”的 中西文化交融 审视东吴大学之发展前史以及大学堂之创办,其背景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、列强入侵的时局,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势下。孙乐文初来苏州时,也是抱着“望我华人同应世界潮流,恒以灌输西学为职志”的目的,“仿西国学校之意旨”,创办中西书院的。东吴大学自成立起,一直秉承延续着中西并举的教学思路。与早年的一些教会学校相比,“孙校长设学,所最注重者,我国之国学”“先生设学,首重国文”,这在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能清晰地感受得到,在孙乐文的支持下,中国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由黄人撰著,诞生于东吴大学。孙乐文校长曾对中国学生说:“中国学生当首取祖国固有之国粹,发挥之、光大之,不应专习西文,置国本于不顾。”对校中教职员、学生或是社会各界人士,只要“语及求学一事”,必谆谆谓之曰:“地球面上无论何国欲图自强,其间重要关系,全在精究本国之学术,从未见有放弃本国学术,而其国得以兴盛者。今我以西学相饷,不过欲中国青年于本国学术外,得有互相考证之可能,免除中外膈膜而已。事有本末,功有体用,能勿误认,庶乎近之。” 孙乐文校长“相互考证,免除隔膜”的这一观念,比之晚清以来,中国学术思想界一直纠缠不清的“中西体用”问题的争论,确实要通达许多。中西文化之间只有在相互了解、相互沟通的情况下,才能够相互促进,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。正是在这种自由会通的学术氛围中,国文教习黄人在讲授《中国文学史》课程时,就向学生介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,并运用比较文学的观点、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,当之无愧成为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先行者。
对于中国传统文化、传统节日,孙乐文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和尊重,在东吴大学的假日安排中,每年除了“暑假约六礼拜,年假约四礼拜”,也安排“端午、中秋两大节各假三天”。对于苏州本地文化,东吴大学的主事者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,1920年学校设立了吴语科,系统地从事吴语及文化的教学和研究。如何立足中国文化、立足吴地,结合地方科学、文化、经济的发展,积极推进教学、研究的深入发展,即便在今天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。 全人教育、“高尚教育”理念的全面实施。 东吴大学肇造之初,就把《圣经》中的“Unto a fullgrown man”这句话作为校训,强调对学生人格、素养的全方位培育,实现为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理念。1927年,杨永清当选为第一位华人校长,把“养天地正气,法古今完人”作为中文校训,与英文校训相呼应。虽然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,但注重学生人格的塑造,“其管理学务,一主宽仁”(嵇绍周《东吴大学校监院孙公传》)。校规中明确说:“本学堂以君子待人,设规极简,务望诸生亦以君子自待,勿负本学堂厚意。”(《志成绩》)在纪念孙乐文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演讲中,东吴大学第三届毕业生杨惠庆将这种教学总结为“高尚教育”和“模范教育”。在这种全人教育、“高尚教育”理念的指引下,早期东吴大学的教学活动,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,对教师学生的道德品行、科学精神、身体素质、审美以及演说辩论等诸方面的能力尤为重视。 《志成绩》部分中对学生在体育、辩论、音乐诸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尤为详细,无须赘述。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,这都有赖于东吴大学早已将这些视为涵养学生人格、发扬学校精神的主要途径。试以艺术教育为例,略作说明。所谓“陶情淑性,莫善于音乐”,故而音乐教育、艺术熏陶在东吴大学的人才培养中意义非凡。其中不乏有学生自发成立的民族弦乐社团(诸如景倕会等),更有“为学校所规定,与体育之兵操并重”的军乐队,校方的重视,其目的是为“发扬本校之精神者也”。(《东吴年刊(1922年)》)此外,还有在中国大学戏剧社团中“元老级”的东吴剧社,一直把戏剧的“意义与价值”定位在于“表现人生”的艺术,以期“对于社会亦略有贡献”,也成为学校化育学生的重要舞台。(《1922年东吴年刊》)这正是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传统之继承与发扬,“吟哦讽咏,浸润优悠……孰谓其无益于世道也哉?”(元·刘埙《隐居通议》卷六) 更有值得大书一笔的是,东吴大学的青年会,“联合同志,各以学问、道德相砥砺”,以“救世之旨”创办了惠寒小学。1910年,青年会在望星桥堍的一间小屋中创办了“嘉惠寒畯”的惠寒小学,历经“艰难辛苦,缔造经营”,东吴学生中“愿牺牲一己而于教育事业上具热心者”,积极充当惠寒小学的“义务教员”,到1922年的时候,惠寒小学的学生已达72人之多。 通识教育的初步探索和实践。 《1918年东吴英文年刊》上有一张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的兵操图,背景中礼堂门楣上挂着“学重淹通”的匾,这自然可以视为东吴系学校(从中学到大学)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方面的重要理念。 自北洋政府“壬戌学制”颁布之后,东吴大学严格按照规定,实行了学分制。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,明确提出了“主科”和“副科”相对应的学分要求。积极探索“主、副科”制度(即今天之“主修—辅修”),推行通识教育。在学籍规定中,还专门列有《主科—副科之规定》,明确讲到“主科—副科”制的目的是“俾所学得臻融会贯通之境”,且规定“主科至少须有二十四学分,副科至少须有十四学分。”学生在完成本专业所列的必修的“主科”外,还必须按规定完成一定数量与主修课程相关的“副科”,比如: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“得以任何文科学程为副科”,教育科的学生“得以文理科任何学程为副科”,生物学和化学的学生“得以他种理科学程或算学为副科”。 这种让学生“臻融会贯通之境”的通识教育理念,在此后历年的学程规范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。如今通识教育依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难点,百年前东吴大学的一些做法,对今天的大学教学改革或许会有些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吧。
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。 据《东吴六志》记载的史实,当时的主事者极具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,这应是东吴校史遗产和学术传统中最可宝贵,也最值得传承的。 早在创立之前,来华传教的林乐知、孙乐文等人就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,实乃“尚在旧教育时代”,创办的所有学校都“不曰学堂、学校”,而是以当时中国人更易接受的“书院名之”。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办学规模和影响的扩大,以及旧式科举考试的逐渐式微,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诸位先生,“知华人之风气已开,设学时机已到,遂开始为筹备大学之运动焉”。就在筹备创立东吴大学堂的过程中,皆选派“林乐知先生、柏乐文先生等旅华较久、熟悉华事者,会同酌办”,他们并没有急于求成,“不敢鲁莽,先于我国社会、官厅各方面屡加探讨,迨至已有把握,即拟就计划书,先商之于学属部(即今校董部),再商之于差会”。在东吴大学办起来之后,孙乐文为首的主事者也是审时度势,循序渐进地推进着大学堂的发展。“校中规程,历年多有修改,屡经修改”,逐步完善,最终建立起较为合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教学体系,在当时的中国实属领先,一时群彦辈出,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。 正是这种精神,早年的东吴大学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大学筚路蓝缕的艰辛,也引领着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,在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“第一”和“最早”:东吴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校之一、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;拥有最早的硕士学位获得者、最早的大学学报《学桴》(《东吴月报》)、最早的大学文学社团刊物《雁来红》、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《普通百科新大辞典》;第一部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巨著《中国文学史》属全国首创的新鲜事物,也诞生于此。
|
|||||
| 【我要打印】 【关闭窗口】 |